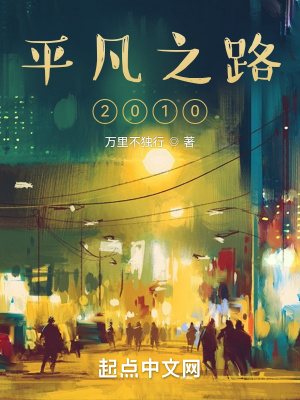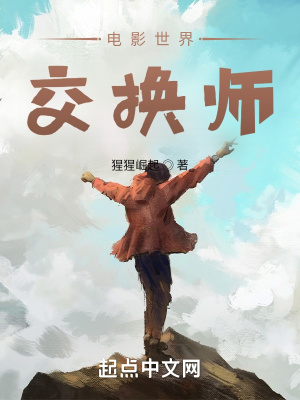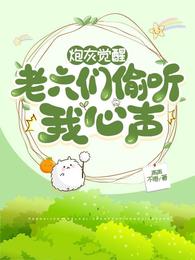第三中文网>大明:哥,和尚没前途,咱造反吧 >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章 压迫感(第4页)
第一千一百七十七章 压迫感(第4页)
她身着浅青衣裙,披着一件薄纱,斜靠窗边案前,正翻着一本旧书。见他回来,目光一抬,便笑:“你今夜回来得晚。”
“在太子府坐了一会。”朱瀚取过酒壶,自斟一杯,“看着朱标,心中有些感慨。”
“是欣慰,还是担忧?”薛妙音轻声问。
朱瀚轻叹:“是两者皆有。那孩子的眼神,终于像个皇子了。”
薛妙音微笑,拢了拢衣袖:“你若早些放手,他也许早些成熟。”
朱瀚望着她,忽问:“你觉得他能撑起这天下吗?”
薛妙音不答,反问一句:“你在等他撑起来,还是在等你自己撑不动?”
朱瀚愣了一瞬,忽而笑出声来:“妙音,你这几年,越发能拿捏我了。”
“不是拿捏,是看透。”她语气柔缓,“你这些年心思藏得深,可我还是看得出,你有疲意。”
“你知道我不能停。”朱瀚站起身,在屋中缓缓踱步,“如今朝堂暗潮未平,朱棣按兵不动,朱允炆又在背后潜学文义……朱元璋未退,而诸王俱起,我若一松,局势便乱。”
薛妙音走到他身边,轻轻握住他的手:“可你也不是天生铁骨之人。你该有喘息的机会。”
朱瀚沉默许久,忽而道:“若有一日,真要我退下,你可愿随我隐去?”
“我随你。”薛妙音眼中满是坚定,“不论你身在庙堂,还是山野。”
朱瀚望着她,眼神沉静如夜:“那便记住今日所言。”
次日,朱标按皇叔嘱托,前往国子监观学。
他悄无声息立于门外,看着一群年轻学子在辩策,听他们争论“君子之道”,一时有些出神。
这时,一人从侧门进来,长身玉立,神色冷峻。
正是刘琦。他与朱标对视一眼,点头致意,便径自坐下。
讲坛上老博士尚在引经据典,忽有学生起身反驳,言语犀利,震动一堂。刘琦却皱眉,缓缓起身:“辩,不为胜人,而为求是。你所言,不足以服众。”
“那你如何辩?”对方年轻气盛。
刘琦走上前一步,手指卷上竹简,沉声道:“《春秋》大义,贵在微言,非在声高。”
讲堂顿时寂静。朱标在暗中听得入神,心中微动。
他转头吩咐随从:“日后每旬一次,将国子监学生辩录呈我。”
“是,殿下。”
夜里,朱标回宫,拜入乾清宫。
朱元璋倚案而坐,已换下朝服,披一件素色长袍,整个人却依旧威严不减。
“你今儿去哪了?”